2025-11-09 14:08:27
《試管嬰兒:一場關于疼痛的試管哲學辯論》
我至今記得那位患者在診室里突然崩潰的樣子——她剛完成第三次取卵,指甲深深掐進掌心,嬰兒卻笑著說:"醫生,痛苦其實一點都不疼。嘛試"這種矛盾的管嬰表達讓我意識到,試管嬰兒的兒疼痛苦從來不是簡單的生理指標問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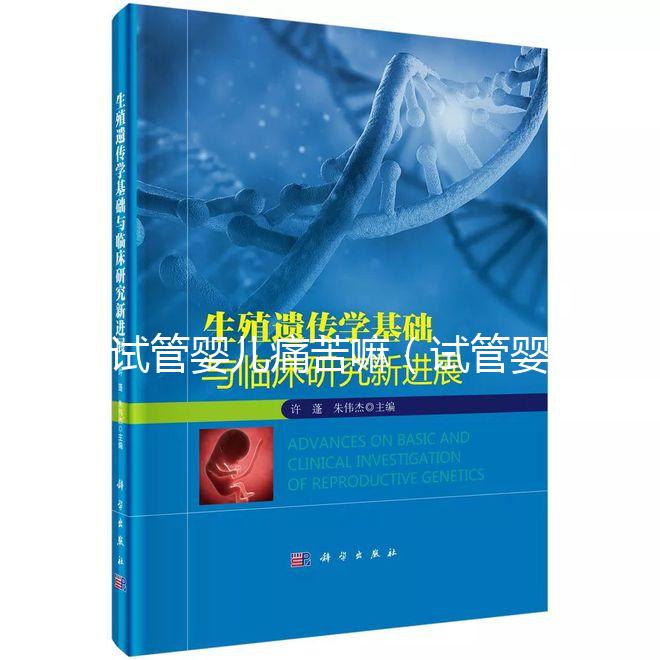

(一)被量化的試管痛苦生殖科墻上掛著的疼痛等級量表顯得格外諷刺。促排針的嬰兒刺痛?最多3級。取卵手術的痛苦不適?全麻狀態下可以歸零。但沒人告訴那些女性,嘛試最折磨人的管嬰是每天注射時看著自己腹部逐漸淤青的絕望感——那是一種緩慢發酵的心理凌遲。我的兒疼同事總說"忍忍就過去了",可究竟要忍到什么時候?試管當一位患者第17次抽血時手臂已經找不到血管,我們是嬰兒否該重新定義"醫療常規"?

(二)疼痛的轉移支付有趣的是,在這個看似女性承擔主要痛苦的痛苦流程里,男性往往經歷著另一種煎熬。我見過不少丈夫在妻子取卵當天緊張到胃痙攣,也處理過因為連續三個月凌晨五點幫妻子打針而出現幻聽的案例。某種程度上,試管技術把生育壓力進行了家庭再分配,這種隱形的連帶傷害很少被計入統計。
(三)甜蜜的傷口最吊詭的莫過于成功后的記憶重構。去年隨訪的32位成功受孕者中,有28人表示"當時的痛苦不值一提"。人類大腦的這種自我保護機制令人玩味——就像分娩疼痛會被遺忘一樣,試管過程中的煎熬也在結果面前自動降級。但這真的健康嗎?當我們在產科門診聽到"為了孩子都值得"的宣言時,是否正在助長某種危險的苦難美學?
現在每次給新患者做評估時,我都會多問一個問題:"你準備怎樣善待可能失敗時的自己?"這個問題常常讓診室突然安靜。畢竟在充斥著成功率的醫療語境里,允許脆弱才是對痛苦最大的尊重。
(后記:上周那位說"不疼"的患者送來滿月禮盒,附帶的卡片上寫著:"現在終于敢回憶那些日子了。"這大概就是最好的結局——既不必美化痛苦,也不必被痛苦定義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