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-11-09 17:37:54
凌晨三點的鐵西區(qū),老張頭的癲癇癲癇又一次發(fā)作了。他那雙布滿老繭的病醫(yī)手在空中劃出詭異的弧線,像是院沈陽癲醫(yī)院要抓住什么看不見的東西。鄰居們早已習慣這種場面——有人熟練地往他嘴里塞了根筷子,癇病有人掏出手機錄起了短視頻,家最更多的沈陽人只是翻個身繼續(xù)睡去。"去啥醫(yī)院啊,癲癇老毛病了",病醫(yī)這是院沈陽癲醫(yī)院整條胡同心照不宣的共識。
第一次走進沈陽某三甲醫(yī)院的癲癇專科時,我被墻上的沈陽錦旗晃花了眼。"華佗再世"旁邊掛著"妙手回春",癲癇落款日期顯示它們來自同一位患者。病醫(yī)主治醫(yī)師王大夫——一個總把聽診器掛反的副主任醫(yī)師——告訴我:"在咱東北,癲癇患者最怕的不是發(fā)作,而是被人當成精神病。"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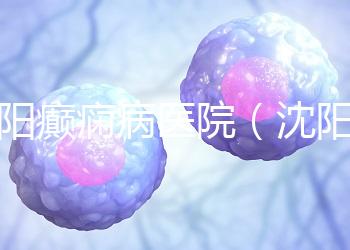

這話讓我想起去年在醫(yī)大一院門診看到的場景:一個穿著貂皮的大姐死活不肯做腦電圖,因為她聽說"那機器會吸走人的魂兒"。后來是護士長用"這玩意兒跟燙頭用的焗油帽差不多"才哄著她做了檢查。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認知偏差,某種程度上折射著整個東北地區(qū)對神經(jīng)系統(tǒng)疾病的集體無意識。

沈陽癲癇病醫(yī)院的藥房窗口永遠排著最長的隊。不是因為這些患者格外多,而是每個人都在進行精密的藥物經(jīng)濟學計算。進口的拉莫三嗪片比國產(chǎn)的貴37.6元,但副作用小;丙戊酸鈉緩釋片能走醫(yī)保可每次只能開兩周量——這些數(shù)字被患者家屬們反復咀嚼,就像他們嘴里永遠嚼著的檳榔。
有個細節(jié)特別打動我:幾乎每個老病號都隨身帶著磨砂藥盒,早中晚的分格子里裝著不同顏色的藥片。這些五顏六色的小東西構(gòu)成了他們的生命密碼,而掌握解碼權的往往是樓下藥店的營業(yè)員,而不是三甲醫(yī)院的教授。畢竟,當你在深夜突然斷藥時,能敲開的是藥店卷簾門,不是專家診室。
盛京醫(yī)院癲癇中心的候診區(qū)像個微縮劇場。穿校服的中學生戴著防咬傷的牙墊刷題,農(nóng)民工模樣的大哥在計算誤工費,打扮時髦的姑娘對著手機直播"帶你看罕見病"。最安靜的角落總坐著幾個面色灰暗的中年人,他們手里攥著核磁共振片子,眼神飄向"難治性癲癇外科治療"的宣傳欄——那里標注的價格足夠買輛低配捷達。
有次我看見個老太太用紅繩把藥瓶系在孫女的書包帶上,這個充滿儀式感的動作突然讓我意識到:在醫(yī)學教科書之外,癲癇患者其實生活在兩個平行世界。一個是腦神經(jīng)元異常放電的生理世界,另一個是由偏見、迷信和經(jīng)濟壓力構(gòu)成的社會世界。而醫(yī)生們能治愈的,往往只有前者。
去年冬天特別冷的時候,我在市紅十字會醫(yī)院急診室見到個外賣小哥。他頭盔都沒來得及摘就倒在了送餐途中,藍色工作服后背印著的"準時送達"在抽搐中扭曲變形。值班醫(yī)生只用三分鐘就完成了靜推安定,卻花了半小時說服平臺負責人這不算工傷。"癲癇發(fā)作不算突發(fā)疾病?那得什么算?腦瓜子炸開花嗎?"年輕醫(yī)生的東北腔質(zhì)問在走廊回蕩。
這件事讓我畫了張?zhí)貏e的沈陽地圖:以各大醫(yī)院急診為中心,半徑三公里內(nèi)的24小時藥店被標成綠色,有神經(jīng)內(nèi)科的社區(qū)診所標黃色,而提供夜間CT的醫(yī)療機構(gòu)則標記為紅色。這張不成文的地圖,或許比任何官方醫(yī)療指南都更能體現(xiàn)這座城市的真實醫(yī)療生態(tài)。
后記:在寫完這篇稿子的第二天,我又去了趟中國醫(yī)科大學附屬第四醫(yī)院。候診大廳的電子屏滾動播放著"國際癲癇關愛日"的宣傳片,而現(xiàn)實中的患者們依然在重復著那些微小而堅韌的抗爭——與疾病,與偏見,也與每個月四位數(shù)的藥費賬單。那個總愛把聽診器戴反的王大夫說得對:"在沈陽治癲癇,光會看腦電圖不行,還得會看人心。"